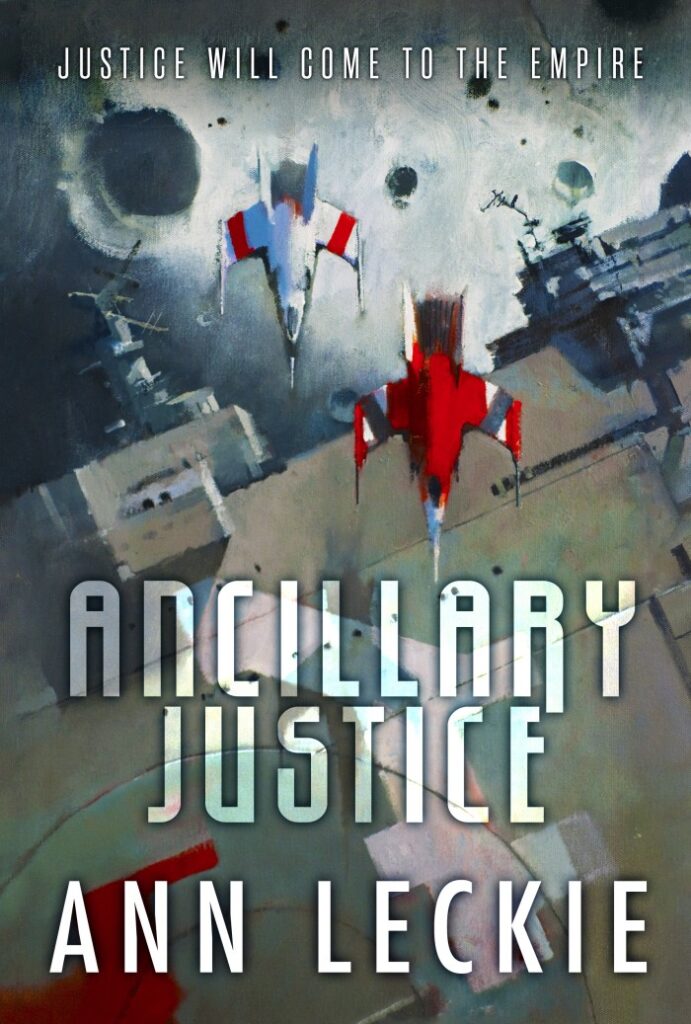1
那具屍體赤身裸體,臉朝下趴著,膚色死灰,濺出的血跡染紅了周圍的白雪。氣溫是攝氏零下十五度,數小時前,一場風暴才剛停歇。在蒼白的晨曦下,積雪平滑無痕地鋪展著,只有幾道足跡通往附近一棟冰磚屋。那是一間酒館,或者說,是這座城鎮裡充當酒館的地方。
向外伸展的手臂,從肩膀到髖部的線條,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。但我應該不認識這個人,這裡我誰也不認識。這是一顆寒冷孤寂星球上被冰封的窮鄉僻壤,與拉契人所謂的文明觀念可說是天差地遠。我之所以會在這顆星球的這座小鎮,純粹是因為我有急事要辦。街上的屍體並非我該關心的事。
有時候,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某些事。即使過了這麼久,這種無所適從、下一刻沒有指令可以依循的狀態,對我來說仍是件新鮮事。所以我無法向你解釋,為什麼我會停下腳步,用一隻腳抬起那光裸的肩膀,好讓我能看見那個人的臉。
儘管她全身凍僵、滿是瘀傷又血跡斑斑,我還是認出了她。她名叫賽瓦登.文達伊(Seivarden Vendaai),很久以前曾是我的軍官,年輕的尉官,最終晉升並獲得自己的指揮權,統領另一艘船艦。我本以為她已經死了一千年,但她千真萬確地就在這裡。我蹲下身,探測她的脈搏,尋找極微弱的氣息。
還活著。
賽瓦登.文達伊已與我無關,不再是我的負責對象。而且,她從來就不是我喜歡的軍官之一。當然,我曾服從她的命令,而她也從未虐待過任何附屬體,從未傷害過我的任何一個分段體(不像某些軍官偶爾會做的那樣)。我沒有理由對她抱持厭惡感。恰恰相反,她的言行舉止在在顯示出她是個受過良好教育、出身名門且教養極佳的人。當然,她不會針對我——我不是個人,我是一件設備,船艦的一部分。無論如何,我從未特別喜歡過她。
我起身走進酒館。這地方很暗,冰牆原本的白色早已被污垢或更糟的東西覆蓋。空氣中瀰漫著酒味和嘔吐物的氣味。一名酒保站在高高的吧台後面。她是當地人,又矮又胖,臉色蒼白,眼睛睜得老大。三名酒客懶散地癱坐在骯髒的桌邊。儘管天氣寒冷,他們卻只穿著長褲和鋪棉襯衫——現在是尼爾特星(Nilt)這個半球的春天,他們正在享受難得的暖和天氣。他們假裝沒在看我,儘管他們肯定看見我在街上,也知道我進來的原因。很可能他們之中有一人或多人涉入其中;賽瓦登在外面待的時間不長,否則她早就死了。
「我要租一輛雪橇,」我說:「再買一套失溫急救包。」
我身後一名酒客咯咯笑了起來,用嘲弄的語氣說:「你還真是個強悍的小姑娘啊。」
我轉身看著她,端詳她的臉。她比大多數尼爾特人還高,但跟他們一樣又胖又白。她的塊頭比我大,但我比她高,而且我的力氣也遠比外表看起來大得多。她沒意識到自己惹上的是什麼樣的人。從她襯衫上縫製的稜角分明的迷宮圖案來看,她大概是個男性。我不是很確定。如果我身在拉契(Radch)領域,這點小事根本無關緊要。拉契人不太在乎性別,而他們說的語言——也就是我的母語——也完全沒有性別標記。但我們現在說的這種語言卻有,要是我用錯了稱謂形式,可能會給自己惹上麻煩。用來區分性別的線索會因地而異,有時甚至天差地別,而我幾乎從未理解這些線索,這讓情況變得更糟。
我決定什麼都不說。過了幾秒鐘,她突然在桌面上找到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似的,低下了頭。我大可以當場毫不費力地殺了她。我發現這個念頭頗具吸引力。但眼下,賽瓦登是我的首要之務。我轉回身去面對酒保。
她懶洋洋地倚著吧台,彷彿剛才的插曲從未發生過似的說道:「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?」
「一個能租雪橇、賣失溫急救包的地方。」我仍安全地待在不需要標示性別的語言領域裡說話:「多少錢?」
「兩百申。」我敢肯定,這至少是市價的兩倍。「雪橇的錢。它在後面,你得自己去拿。急救包另外再一百。」
「要完整,」我說:「沒用過的。」
她從吧台下拿出一個,封條看來完好無損,同時道:「你外面那個同伴還欠著帳呢。」
也許是謊話,也許不是。無論如何,數字肯定是信口開河。「多少錢?」我問。
「三百五十。」
我可以想辦法繼續避免提及酒保的性別。或者,我也可以猜一下。最糟的情況,機率也不過是一半一半。「你還真是信得過人啊,」我說,猜是個男的:「竟然讓這麼一個窮鬼(我知道賽瓦登是男性,這點倒是簡單)欠下這麼大一筆債。」酒保沒說話。「六百五十,全結了?」
「嗯,」酒保說:「差不多吧。」
「不,就是全部結清。我們現在就說定。如果事後有人來跟我要更多錢,或想搶我,他們就得死。」
一片沉默。接著,我身後傳來某人的吐痰聲:「拉契敗類。」
「我不是拉契人。」這是實話。你必須是人類,才能算是拉契人。
「他是,」酒保說,朝門口的方向微微聳了聳肩:「你沒有口音,但你身上有股拉契人的臭味。」
「那是你們給客人喝的餿水酒的味道。」我身後的酒客們發出幾聲叫囂。我伸手進口袋,抓出一把代幣,扔在吧台上。「零錢不用找了。」我轉身準備離開。
「你的錢最好是真的。」
「你的雪橇最好也像你說的一樣在後面。」說完我便離開了。
先處理失溫急救包。我把賽瓦登翻了過來。然後我撕開急救包的封條,從卡片上掰下一顆內服劑,塞進她那血淋淋、半凍僵的嘴裡。卡片上的指示燈一轉綠,我便攤開那張薄薄的包裹毯,確認電力充足後,將它裹在她身上,啟動開關。接著我到後面去拿雪橇。
沒有人暗算我,這很幸運。我還不想留下屍體,我不是來這裡惹麻煩的。我把雪橇拖到前面,將賽瓦登搬上去,考慮過要不要脫下我的外衣蓋在她身上,但最後我認為,比起單獨使用失溫包裹毯,這樣做也好多不了多少。我啟動了雪橇的動力,隨即離去。
我在鎮邊租了個房間,那是一排十幾個灰綠色、髒兮兮的組合式塑膠屋,每間都是兩公尺見方的立方體。房裡沒有寢具,毯子和暖氣都要另外收費。我付了錢——為了把賽瓦登從雪地裡救出來,我已經浪費了一大筆荒唐錢了。
我盡可能地擦掉她身上的血跡,檢查了她的脈搏(還在)和體溫(正在回升)。曾幾何時,我不用多想就能知道她的核心體溫、心率、血氧濃度、荷爾蒙水平。只要我心念一動,就能看見她身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傷勢。現在,我瞎了。她顯然被毆打過。她的臉腫脹,軀幹上滿是瘀傷。
失溫急救包裡附有一劑非常基礎的校正劑,但只有一劑,而且只適用於急救。賽瓦登可能有內傷或嚴重的頭部創傷,而我頂多只能處理割傷或扭傷。運氣好的話,我要處理的就只有失溫和瘀傷。但我沒有太多醫療知識,再也沒有了。我能做出的任何診斷,都只會是最基本的那種。
我又將一顆內服劑塞進她喉嚨,再次檢查——考慮到她的處境,她的皮膚已不比預期冰冷,也沒有濕黏的感覺。撇開那些瘀傷不看,她的膚色正逐漸恢復為較為正常的棕褐色。我拿了一容器的雪進來融化,把它放在一個角落,希望她醒來時不會踢翻,然後才出門,並隨手鎖上了門。
太陽在天空中升得更高,但光線幾乎沒有變強。此刻,更多的足跡破壞了昨夜暴風雪後平整的雪地。一兩個尼爾特人正在四處活動。我把雪橇拖回酒館,停在後面。沒有人來攔我,漆黑的門口也沒有傳出任何聲響。我朝鎮中心走去。
人們在外頭忙著做生意。幾個又胖又白穿著長褲和鋪棉襯衫的孩童,互相踢著雪玩。他們停下來,睜著那雙看起來總是很驚訝的大眼睛,盯著我看。大人們則假裝我根本不存在,但經過我身旁時,他們的眼神卻會飄向我。我走進一間商店,從這裡稱得上是白晝的戶外走進昏暗的室內,一股寒意襲來,僅僅比外面暖了五度。
十幾個人正站著聊天,但我一進門,他們便瞬間鴉雀無聲。我意識到自己臉上沒有任何表情,於是調整了臉部肌肉,擺出一個愉快而又不置可否的表情。
「你要什麼?」店主咆哮著問。
「這幾位客人想必比我先到。」我邊說邊希望在場的是男女混雜的群體,這樣我的句子才不會用錯稱謂。回應我的只有一片沉默。「我想要四條麵包和一塊板油。另外還要兩套失溫急救包和兩劑多功能校正劑,如果有的話。」
「我有十包裝、二十包裝和三十包裝。」
「請給我三十包的。」
她將我買的東西堆在櫃檯上說:「三百七十五。」我身後傳來一聲咳嗽——我又被敲竹槓了。
我付了錢便離開了。孩子們仍舊在街上玩,笑鬧著。大人們依舊從我身旁走過,彷彿我根本不存在。我又多去了一個地方,畢竟賽瓦登需要衣服。然後我回到了房間。
賽瓦登依舊昏迷不醒,就我所見,也仍然沒有任何休克的跡象。容器裡的雪大部分都融化了,我把半條硬得像磚塊的麵包放進去浸泡。頭部受創和內臟損傷是最可能的危險。我打開剛買的兩個校正劑,掀開毯子,將其中一個放在賽瓦登的腹部上,看著它融化成一灘液體並延展開來,最後硬化成一層透明的外殼;另一個則敷在她臉上看起來瘀傷最嚴重的那一側。等那片也硬化後,我脫下外衣,躺下睡了。
七個半小時多一點之後,賽瓦登動了一下,我也隨之醒來。「你醒了嗎?」我問道。我敷上的校正劑固定住了她一隻眼睛和半邊嘴巴,但她臉上的瘀傷和腫脹已消退許多。我思索了一下該擺出什麼樣的表情才恰當,然後便展現出來。「我在雪地裡的一間酒館前發現了你,你看起來需要幫助。」她發出微弱而沙啞的呼吸聲,卻沒有把頭轉向我。「你餓嗎?」沒有回答,只有空洞的凝視。「你的頭有撞到嗎?」
「沒有。」她輕聲說,臉上表情放鬆而無力。
「你餓嗎?」
「不餓。」
「你上次吃飯是什麼時候?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她的聲音很平靜,沒有任何起伏。
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起來坐正,讓她靠著灰綠色的牆壁,一邊提防著她會癱倒下來,一邊避免造成更多傷害。她坐穩了,於是我便用湯匙,小心地繞過那片校正劑,慢慢將一些麵包泡水的糊狀物餵進她嘴裡。「吞下去。」我說,而她也照做。我就這樣餵了她半碗,然後自己吃了剩下的,並又拿了一盆雪進來。
她看著我把另外半條硬麵包放進盆裡,卻什麼也沒說,臉上依然一片平靜。「你叫什麼名字?」我問。沒有回答。
我猜她吸了「嗑夫」(kef)。大多數人都會告訴你,嗑夫會抑制情緒——它確實如此——但它的作用不僅於此。曾幾何時,我能夠精確地解釋嗑夫的作用和原理,但我已非昔日的我。
就我所知,人們吸食嗑夫是為了停止感受某些事物。或者因為他們相信,一旦排除了情感,就能獲得至高無上的理性、純粹的邏輯、真正的頓悟。但事情並非如此運作。
把賽瓦登從雪地裡拖出來,耗費了我本就捉襟見肘的時間和金錢,而這又是為了什麼?如果放任她不管,她會再給自己找上一兩劑嗑夫,溜進另一間像那樣骯髒的酒館,然後讓自己死得透徹。如果那正是她想要的,我無權阻止她。但如果她一心求死,為什麼不做得乾淨俐落一點,像任何人會做的那樣,去登記意願,然後找個醫療官了結?我不懂。
我不懂的事情還有很多,而假裝人類的這十九年,教給我的東西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多。